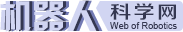6月30日,在深圳举办的科技创新院士报告厅活动上,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京大学副校长郑海荣以《脑机接口与智慧医疗》为题,分享了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前景。他认为,作为生物智能发展抓手之一的脑机接口技术,应该向无需手术的“无创”方向关注和探索。
郑海荣院士演讲 郑海荣提到,医学是全世界产生数据最多的领域之一,也是最需要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域之一。医疗数据具有多源性、海量性、多样性、实时性、复杂性等特点,利用人工智能手段整合、分析和处理复杂的健康和医疗数据,可以推动疾病机制研究、大数据融合、精准诊疗、个体化治疗及新药靶点研发。 他表示,人工智能带动生物医学技术变革,而脑机接口正是其中的重点发展方向。人工智能时代的本质是数据变成了生产力,而最智能和最多的数据就存在于人的大脑里,它不仅是一个器官,更是一个可以发出生物信号的机器,是超级生物计算机。未来,脑机接口将成为真正能够解决医疗问题的技术,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最终走向生物智能。 侵入式脑机接口需重新审视 什么是脑机接口?郑海荣以科幻电影《阿凡达》为例来阐释。当纳美人要骑着伊卡兰翼龙飞行时,只需将二者的“辫子”连接在一起,便可实现意念相通。无需语言的交流,飞龙便可根据纳美人的意愿飞往人心中想去的地方。这里的“辫子”就类似一个脑机接口。“就是把脑子里的想法——也就是信号导出,让其控制机器人等设备。”郑海荣解释道。 据了解,脑机接口分为侵入式、非侵入式、半侵入式三种类型。 侵入式脑机接口即通过外科手术将微型电极或传感器穿透颅骨、硬脑膜,并植入脑实质,直接记录单个神经元的电活动信号。 近期,马斯克旗下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发布的最新研究方向——计划在言语皮层植入电极,正是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代表,更是将性能的追求推到了极致。 2025年上半年,其相关临床研究中的患者,已不仅能用意识控制光标收发邮件,甚至可以操作复杂的CAD软件设计机械零件,乃至驱动一台真实的特斯拉擎天柱机器人手。这一系列成果,清晰地展示了从简单二维光标控制,迈向复杂多自由度机器人操控的技术跃迁。 半侵入式脑机接口则以Synchron公司和Precision Neuroscience公司为代表。 2025年4月,Precision Neuroscience公司的产品“第7层皮质接口”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FDA)的510(k)许可,可用于最长30天的临时植入,为其在术中脑图谱绘制等临床应用中进行早期商业化奠定了基础。 Synchron公司则在安全性验证上取得了关键进展,其在美国进行的一项经FDA批准的首个永久植入式脑机接口试验,于2024年10月公布了核心数据,研究队列中的6名患者,在植入设备12个月后,均未发生由设备直接导致的死亡或导致永久性残疾等严重不良事件。 2025年3月,英伟达宣布与Synchron合作开发名为“Chiral”的认知AI基础模型,旨在建立“大脑基础模型”;同年5月,苹果公司则通过一项新的BCI HID协议,将Synchron的设备原生接入其操作系统,为其提供了触达海量用户的商业化入口。 在郑海荣看来,无论是需要开颅的“硬连接”,还是通过血管的“软连接”,都还未触及问题的本质。侵入式脑机接口是有创的,电极使用寿命有限,并且只能解读电极所接触脑区的信号。其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生物相容性——人脑历经漫长进化形成的精密免疫防御机制,会对植入的异物产生排异反应,导致电极性能随时间显著下降甚至失效。 侵入式脑机接口需重新审视 基于以上理念,郑海荣及其团队所倡导和研究的,是一条截然不同的“无创”之路。其核心逻辑是,通过光、声、电、磁等物理的方法,无需穿透皮肤,就能把大脑里的信息“读”出来。他以浙江强脑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智慧假肢为例,“人直接戴一个护腕,上面有上百个神经电极,便可接收肌电和神经电。喝水、写字等不同意图能够通过AI大模型识别出来,进而控制假肢”。 他将这种关系比喻为“士兵”与“粮草”:“大脑里的神经元是前面打仗的士兵,血管就是后面的粮草,血流跟神经活动有高度的关联性。”他认为,通过高分辨率的成像技术去观察“粮草”的动态,再用AI大模型去反推“战况”,就有可能解码大脑的意图。 这已不是天马行空的构想,郑海荣亦在现场介绍了由他牵头的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一项重大科研项目,正是致力于“用超声波去控制神经元放电”,并已在动物实验中实现了对老鼠记忆和行为的精准调控。 人工智能的最高形容是生物智能 郑海荣之所以对侵入式脑机接口持“重新审视”态度,其根源在于他对人工智能产业未来终局形态的判断。他认为,AI的发展必然经历三个阶段。 第一阶段是“数据智能”,即当前所处的大模型时代,其本质是利用海量数据进行学习和创作。“以前靠人力来掌控这些数据太累、太复杂,”他解释说,“但是计算机让它可感,可以做分析,所以它可以帮我们很多。” 第二阶段是“物理智能”,即AI与机器人、自动驾驶汽车等实体结合,影响物理世界。 第三阶段则是靠脑机接口实现的“生物智能”。他引用了人工智能先驱图灵的论断:“脑与机器的融合并协调工作,是实现人工智能的唯一途径。” 在他看来,“生物智能”才是AI的终极形态,也只有这种由人类大脑直接控制的、与生物智慧深度融合的智能,才能真正降服当前AI模型所暴露出的各种隐忧,确保技术始终朝着有益于人类的方向发展。 当被问及“脑机接口是脑控制机,还是机控制脑?”这个终极问题时,郑海荣表示,“人工智能可能产生强大的威力,如果操作不慎,将对人类造成很大的损害,这是可能的。这也是我倡导发展生物人工智能的原因,因为只有生物控制的人工智能,也就是我们大脑控制的人工智能,才是可以有效降服的。” “未来一定要让‘脑’控制‘机’,而不能让‘机’控制‘脑’。所以大模型的监管规则非常重要,我觉得对这块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。”郑海荣最后说。 文章来源:经济观察报、中国信息化周报等